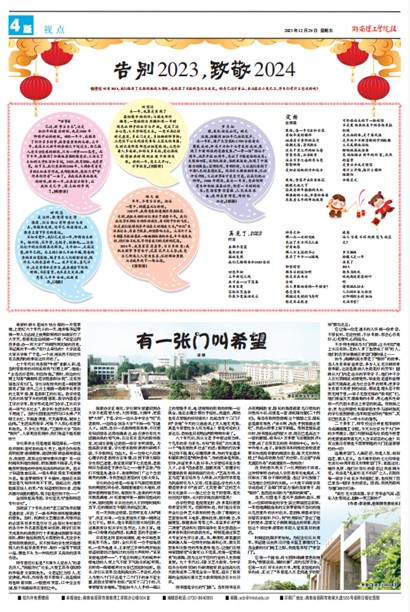奇家岭原本是城乡结合部的一片荒草地,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的一天,地委张书记带领一帮人在山坡上披荆斩棘挥汗如雨穿行了大半天,指着北边山坡画一个圈:“就定这四百多亩,办一所大学!”环顾四周犹疑的目光,书记再次手一挥:“有什么奇怪的?大学就是大家来学嘛!”于是,一个波澜虽然不惊壮怀有点激烈的故事就这样开始了。
七十年代初我告别“牛棚”重新入职,是当时管教育的刘局长将我“打捞上岸”,他说:“去当名好老师,相信你能。”那时,路边的校牌上写着“湖南师范学院岳阳分院”,没有围墙也没有校门。学校分配给我的是一间屋顶露光、门窗透风、三合土地面一遇雨季长青苔的土筑平房,算是教职工的标配。教学楼是几栋农场留下来的砖混建筑,教学内容是学工学农学军,教学形式是开门办学,工农兵学员一律“社来社去”,教学和生活条件之差就不用说了。当时校园里流传四句口头禅:“天晴支农忙,下雨进课堂,天天海带汤,屙屎上山岗。”生活虽然艰辛,可每个人都心有愿景和抱负。不少校友笑谈:“三眼桥大学”简称“眼桥”,人家英国有剑桥,我们难道不能有眼桥?!
学校革委主任是地宣部范部长,一位性格开朗和蔼可亲的高大男士,他开会作报告简明扼要语调鏗锵,说话时眼睛总凝视着远方,我猜想,莫非这位领导常怀诗意?有一段时间我和他住隔壁,晒垫顶棚不隔音,几乎每晚都听到他亦呼亦吼似诉似吟的鼾声。后来才知道他血压高,一遇头晕就得坐下或躺倒休息。每逢带领师生下乡插秧,他站在水田里总是气喘咻咻弯不下腰。说起这些,他常脸露苦恼人的笑:“我知道要控制体重,但每次面对碗里的肥肉,筷子总是控制不住……”
全国恢复高考后,学校定名为“岳阳师范专科学校”。
当耽误了十年机会的“老三届”洗尽泥腿走进教室,开启了一派书声朗朗和弦歌满堂的景象。当时,我讲授文艺理论课,可惜开出的必读书目多半是空对空,出版社争相重印的各类中外名著都是稀缺资源,同学们在寒天或暑热的清晨步行十多里进城到新华书店排队,那时能抢购到几本需要的书,无论学生老师都欣喜欲狂。买不到书的学生便只能借别人的书起早贪黑手抄,每抄一遍等于精读一遍,倒也不失为一种既经济又高效的读书方法。
师专首任校长是“不薄今人爱古人”的著名诗人、“洞庭诗社”社长、大型工具书《辞源》的参编者文家驹先生。文老记忆力惊人,无论讲座、吟诗、作报告都不看稿子,就连摸麻将也眯着双眼,一脸慈祥笑容,口中念念有词,整个场面却尽在掌控之中。
随着办学正规化,学校领导层意识到办大学不光需要大楼、大图书馆、大操坪,更需要“大师”,于是,学校一边从各中学去“挖”名老教师,一边向全国各大学“不拘一格”引进人才。诚然,当好一名教师绝非易事,不仅要有知识储备还得准确表达,站在讲台有优秀话剧演员的精气神,在没有麦克风的阶梯教室,吐词发音能让最后一排学生听清楚。为提高教学质量,学校要求教师讲课科研两不误,不少教师压力山大。有一位给七八级讲心理学的老教师方言难懂,没到下课大部份学生都已退堂,教室里只留下七名党员,老教师深为感动走下讲台与之一一握手言谢:“你们不愧是先进分子,谢谢啊你们!”这个含泪微笑的故事,令我想起王愿坚的《七根火柴》。
学校的办公楼是一栋毫不气派但精美别致的两层红砖小楼,房间里铺着松木地板,楼前种着两棵银杏树,每到秋冬,金黄的叶片随风飘落满地,衬托着地坪里一面鲜花组成的大钟,随时提醒来来往往的人们珍惜时间和当下,它的靓丽至今留在我的记忆里。
有一天我路过楼前,忽然听见有人叫“同学”,我正好奇,一位长者说我们曾一同蹲过五七干校。原来,他文革前在储木场任职,经过再教育分配来学校当传达,人称王爹。他说一口难懂的山西话,长满老茧的手总握一只有尼龙网套的玻璃瓶,瓶中深褐色茶垢长年不洗。当时,全校只有一台手摇电话机,一有外电进来,王爹便三步并作两步跑出楼道朝着估计加统计的方向大声疾呼:“某某某接电话啰——”,于是在响彻云天的喊声中接电话的人便上气不接下气跑来抓起听筒,只听得一阵嘟嘟声对方早已因超时挂断。后来,学校从某单位选购淘汰的二手总机,经办人为要八个门子还是十二个门子的拿不定主意,最后主管领导拍板:“就买十二门子的,凡事要留有余地嘛。”想起如今人人手持一部以上的智能手机,电话视频拍照购物转账一应俱全,谁还去理会那些手摇机、拨盘机、哪怕也有点智能的按键座机?比起当年十二门子的“余地”今天的交通通讯上天入地无死角,真是今非昔比令人叹为观止!要是可爱的王爹还在,恐怕也只有用山西腔啧啧称奇了。
八十年代初,我从文老手中接过接力棒,十几年的亲力亲为,方知“教书匠”治校真是一个“唯有牺牲多壮志”的活:繁琐的行政事务让你不能再心安理得讲课,你的专业追求和履职责任是“两种思维”,你的使命是帮助、引导、保证更多人教好书;大学要培养复合型人才,必备“自由思想,创新灵魂”,管理学校要遵循教育规律而弱行政化;“艺高为师,身正为范”重在培养为人师表,从代际传承看是为民族孵化为人父母,任重道远;学生的人格塑造要多学科“通识”,尤其要靠广泛的艺术和文化滋养……加之社会处于转型期,变化往往比计划快,应对治学挑战谈何容易!
办学经费总是捉襟见肘,许多美好愿景都希望在明天。但即便如此,我们也没有放弃全校公共艺术教育的特色:除了常规的文艺套餐如周末电影、歌咏比赛、联欢晚会、书画展览,服装表演等等之外,丰富多彩的“第二课堂”活动和校园环境净化美化营造出一派青春和美好的勃勃生机。特别是通过非艺术专业学生开设音、美、书、舞课程,审美意识渐渐融入每一位师生的脑海和心灵,激发其想象和发散性的形象思维能力,让他们在精神家园接受“皮囊可以不完美,灵魂一定要高贵”的熏陶,因为这对于任何行业的人生都很重要。九十年代初,《普及艺术教育,为中学培养合格师资》的科研课题荣获全国高校优秀教育成果二等奖全省一等奖,迎来了教育部的全国高校普及艺术教育现场会在本校召开。
图书馆是学校的“门面”。当年图书室只占有两间教室,隐秘的角落藏着几口精致的深色樟木箱,箱里是一套清乾隆线装《二十四史》。每当有教师想借阅这个镇馆之宝,馆长总是面有难色:“善本啊,洗洗手到里面去看吧”,然后从腰带上解下钥匙。等到老馆长退休时,图书馆长成四层大楼,现在已是高达十一层的新馆,藏书从5万多册飞速增加到278万册,成了名符其实的图书情报中心。如今,中外纸本、电子、音像图书和网络捡索给读者带来快捷而崭新的阅读体验,每天无数师生踏上“书山有路勤为径”的台阶,在这座“学海无涯苦作舟”的殿堂里作一瓢畅饮!
改开的春风吹来了一校两制的干训班,这种特事特办的成人学历教育充电模式,不仅解决了部分干部的燃急,也让学校加强了与当地社会经济的关联。一大批干训班学员学成后成了各部门年富力强的当家骨干,而“眼桥”,也因此被戏称为“岳阳的黄埔”。
当然,校园也不是风平浪静的温床,那年,一位即将毕业的学生误立萧墙因言获罪,一年后他满脸沧桑的父亲带着悔不当初的他从几百里外的农村赶来,老泪纵横恳求学校保留其学籍和户口,我“利用职权”答应了他们的要求,望着父子俩蹒跚远去的背影,我深信这个将往事清零的年轻人定有美好的重启。
时间总比脚步更匆匆。为纪念校庆21周年,书记建议由我设计他来监工新建校门。当全新的校门峻工之际,我提笔书写了“希望门”。
它像一个画框,将校园和南湖景色收纳其中。“删繁就简,领异标新”,简约包罗万象;
它像一本打开未来的大书,用笔直坚挺的线条构成,正应了“书籍是人类走向进步的阶梯”那句名言;
它让每一位走进来的人怀揣一份希望,不管长相,无论性别,不分年龄,都会心存美好,心无旁鹜,心向远方。
不少师生闻讯为大门捐款,这些相信“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的人,他们的名字被镌刻在希望门旁的墙上……
如今,南湖的流水带走了“眼桥”的故事,当人生有幸邂逅希望,多少人义无反顾将青春奉献,这就是澹泊人生最美好的芳华!回眸从大门内走出来的莘莘学子,他们中不少人在校期间就成绩斐然,毕业后足迹和业绩遍布天南海北,成为社会各界的精英;更多学生有着不易看到的成就,那就是埋头苦干默默无闻于世,一辈子无怨无悔的“教书匠”们,他们像遍及天涯海角的小草,用心血和生命将一代代后来者送上希望的轨道。我钦佩之余,更为这所曾经和前辈后生参与添砖加瓦的学校感到骄傲:当年略显袖珍的“眼桥”,其实已经具备了一所本科的雏形。
二十多年了,师专经过合并重组华丽转身成湖南理工学院,今天来往穿梭于大门中的少男靓女,他们何曾知道鸟枪换炮今胜昔的光景里凝聚着几代人含辛茹苦的心血?只有这张没有锁也不需要钥匙的大门见证着曾经的一切!
远眺希望门,人海茫茫,物是人非,故知远走,新人正来。当不再年轻的七七级毕业生离校40周年后又相聚希望门下,重温过往,缅怀先贤,他们对母校的眷恋让我感同身受。我虽是“儿童相见不相识”之人,在陪伴每一届学子成长岁月的回忆里,也找到了自己重当一回学生的感觉。因而,我欣然即兴为他们站台打油:
“最愁无本读离骚,学子芳华志气高;苦乐人生等闲过,回眸一笑三眼桥!”
2023.12
(作者:李凌烟,岳阳师专原校长)